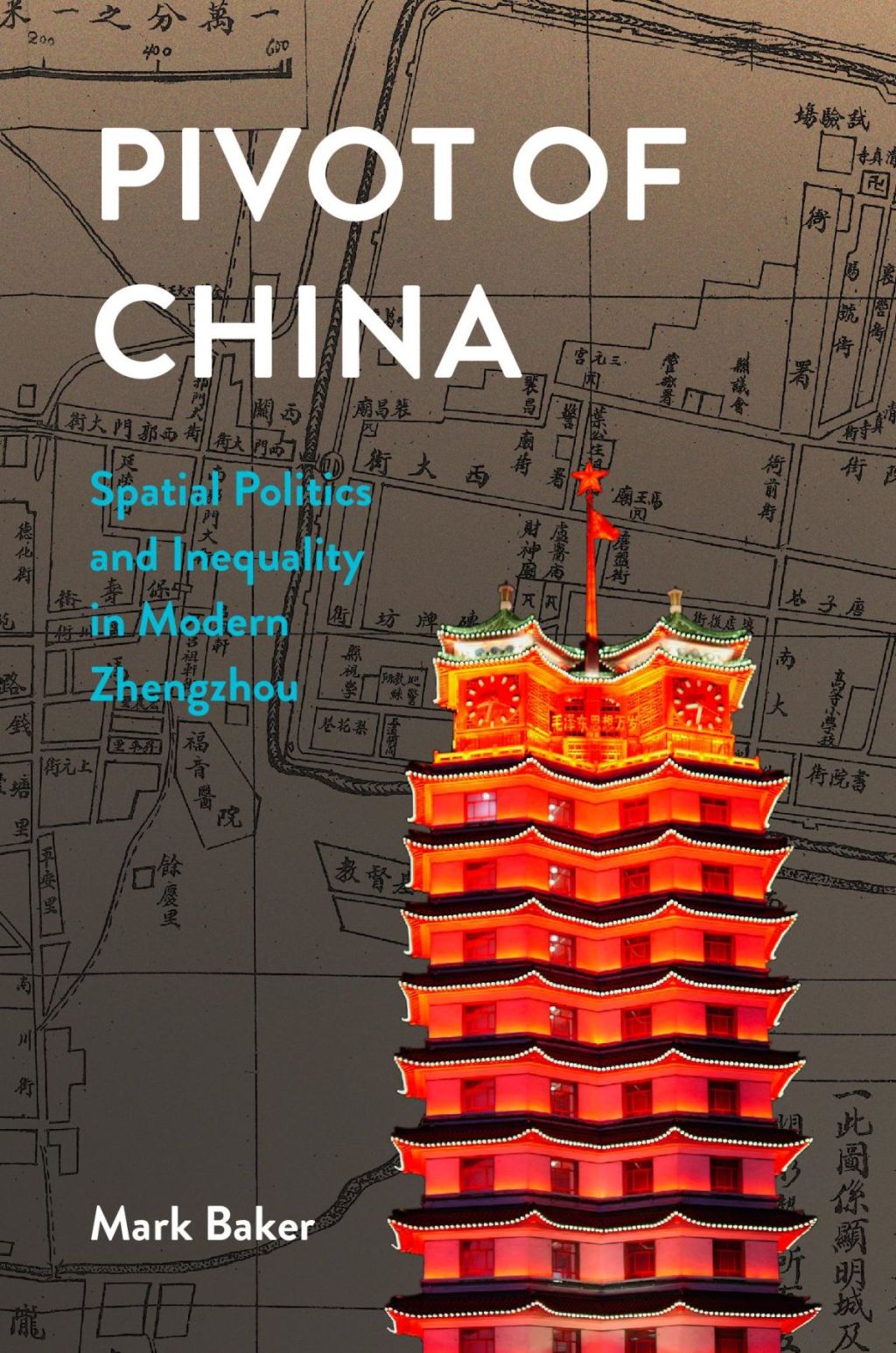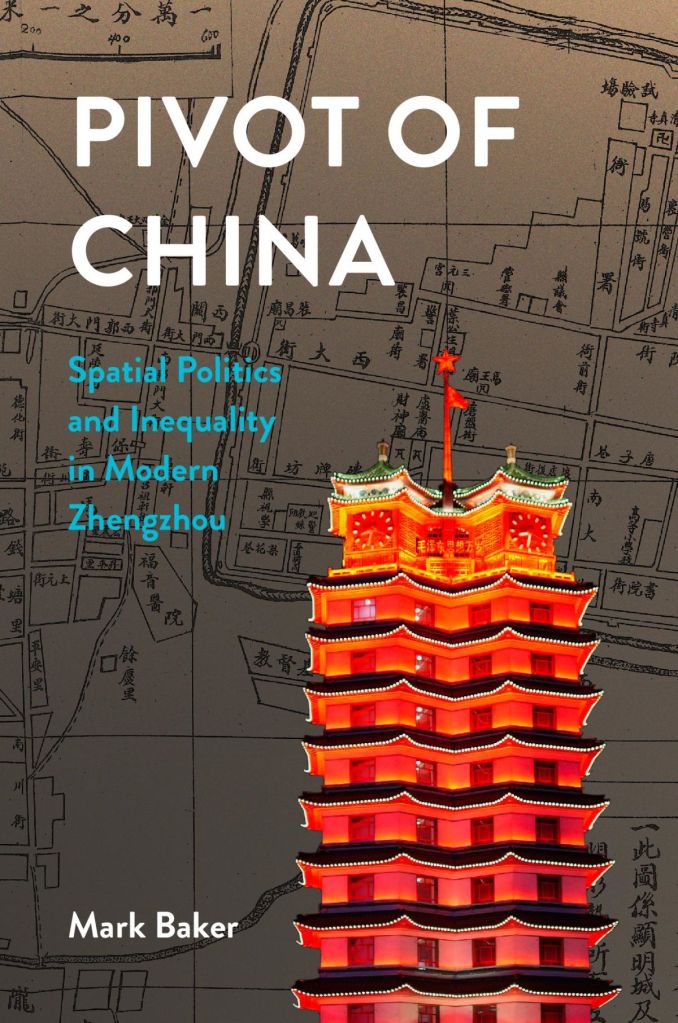按:这是「城识|关键词」栏目的第一篇推送。
近半个世纪前,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关键词》一书,用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词条和例句来阐释变迁中的文化与社会。借助这一系列关键词,威廉斯得以剖析词汇背后的意义历程,描绘社会实践和思想图景的变迁,并厘清他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与意识形态不同,它意在捕捉人们在面对文化与社会变迁时内在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暗流往往以细致而微的方式塑造着社会、艺术、文学和日常生活动态。「城识」公众号力图在方法论上借鉴威廉斯的做法,努力捕捉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和城市变迁过程中的“情感结构”。
我们将遵循威廉斯在书中选择词语的两个标准:一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二是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由此出发,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城市词汇和语言的内部,剖析它们所关联着的城市状况、城市经验和城市进程,更细致地描绘社会变迁的时空图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正在展开但又充满矛盾的“城市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为什么没有中国版的城市政治学”这个问题出发,进一步聚焦“城市”、“空间”与“政治”三个关键词。这一讨论立足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人提供的思想资源,力图展示这些关键词“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的意义和指示性”,同时也充分关注中国的城市(政治)状况,希望能够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别样的分析视角,帮助大家更进一步反思周遭的城市变迁。
一、如何谈论城市政治?
2015年时,有一位城市规划出身的青年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个小节的标题叫《为何没有一门城市政治学课》。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政治学是对城市权力的追问——无论是向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参与决策权力,这都是规划的一个基本关切。以往的规划师往往只埋头画图纸,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城市规划从编制到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的蓝图只能是一张“蓝图”而已。
这是上面那位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而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她引用了一本经典教科书——《城市政治学理论》。如果遵循传统的城市政治学的框架,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必须围绕这几个议题:
(1)政治权力的结构:具体来说就是精英政治和多元论的纷争,城市权力是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里,还是广泛分布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他们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多元的权力格局?
(2)政府组织的结构:民选官员与所谓的官僚制——那些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何种构架和安排最为合理有效?
(3)政治行为的结构: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如何联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主导一个城市的政治决策,改变决策者的政治行为?
(4)空间关系的政治:它立足于古希腊的城邦概念之间的连接去思考,在一个在现代的城市语境里边,有什么样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空间结构和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组织的编排。
但是,这些“正统”的、“经典”的城市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帮我们解答此时此地的城市困惑。《城市政治学理论》——这本书和以它为代表的这个学科——太多地受制于美国的语境。哪怕是在上世纪后半叶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增长机器理论[1]和城市政体理论[2],也与纽黑文或者亚特兰大这样的地方政治状况紧密相关。但是问题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城市政治经验为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削足适履地开展这种“应用”?
也许,我们可以不再谈论“urban politics”,而是把目光转向“politics of the urban”。表述上的微调,可以提醒我们努力把城市政治学从美国语境里摆脱出来,从而去重新思考中国的城市经验——这也正是“把中国作为方法”的题中之义。
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看来,“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作为目的”[3]。换言之,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城市经验(和教训),来与其他国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做更进一步的对话,从而更好地在全球的尺度上理解我们的城市变迁和城市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才是城市政治研究(politics of the urban)真正应该关切的问题。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和政治。
二、关键思想家
在我们的讨论里,有三位思想家扮演关键角色: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
列斐伏尔1901年出生,1991年去世,见证的正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他在早年是法共(法国共产党)的笔杆子,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很多写作是法共的经典文本,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被法共开除出党。在那之后,他的关注重心逐渐从农村问题转移到城市问题。到了196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概念,在 1970年出版了重要著作《城市革命》,1974年出版了代表性作品《空间的生产》。
大卫·哈维在中文世界也许更有名一些。他出生于1938年,在生涯早期主要做定量的地理学研究,并在1969年前后出版过一本关于地理学定量方法的教科书(《地理学中的解释》)。但是,在前往美国的Johns Hopkins大学任教之后,他发现巴尔的摩有很多无家可归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些社会不正义的问题引导他逐渐转向对马克思的阅读。在与《资本论》对话的基础上,哈维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这本书也标志着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的一个批判转向。[4]
多琳·马西生于1940年代,在2016年去世。她在1970和1980年代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提出了著名的“劳动的空间分工”(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理论。面对诸如英格兰东北部“锈带”(Rust Belt)这样的地方,马西提出“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背景,而是组织和体验这些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权力关系、全球联结、地方与身份认同以及空间本身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这些不同的动态彼此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本地苦难。
到了1990年代之后,她开始尝试着把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十分关注与后殖民分析框架的对话。所以当我们阅读她的晚期写作的时候,会发现她的笔触变得更加温柔一些,更关心个体,关心人的处境,关心人的情感,关心偶然性,关心差异。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资源,来逐个探讨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与政治。
三、什么是城市?
什么是城市?如果你依然坚信城市是一个有界空间的话,可能首先需要思考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划定一个城市的边界。
大卫·哈维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非常直接: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不管我们去观察城市还是别的什么产物,我们所观察的此时此刻只是演进过程的一个横截面、一个恒存、一个瞬间,而这个过程是永无止息的。[5]
如果我们把这个产物当成一个一成不变的实体的话,那么就会忽略这个过程的绵延,也就会与真实存在的城市和城市进程失之交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哈维提出了他的“羊皮纸卷”意象。
在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僧侣们需要去书写他们的经书,但是却没有足够的书写材料(羊皮)可用。所以我们现存的很多羊皮纸卷都是被复写了的——它是由很多层面叠加在一起,经常是前一个时代的人写上了一层经书,被后一个时代的人给抹掉,然后在羊皮纸上书写新的内容。
城市也是这样。城市进程在每一个瞬间都会产生它们各自不同的面貌和形态,而在任何一个节点去把它做一个横切面或者纵切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不同的层层层累积的纸层。要想更好地理解立体的城市,我们就需要去理解塑造了这个羊皮纸卷的社会、历史和空间进程。
在与此同时,列斐伏尔的提醒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对city和urban两个术语做了很深刻的区分。[6] 如果说city常常被用来指代具有固定边界的城市空间,那么urban这个形容词就被列斐伏尔拿来表征一个无边的城市。
在他看来,这个无边的城市(urban)是一个弥漫的、全球性的过程,它穿越了所有的空间,而它背后真正具有宰制性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的这个思路其实有一个非常文学化的起源:他非常喜欢读科幻小说,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阿西莫夫,非常经典的《基地》三部曲的作者。在《基地》里,有一座叫做川陀(Trantor)的城市,但它同时也是一整个星球,因为这座城市覆盖了整个星球的表面。
列斐伏尔从这个科幻小说的意象里面提取了一个灵感:在我们的地球上,城市进程是不是正在扩散为一个全球化的进程?能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力量——城市的中心性——成为整个全球变迁的中心环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提出了近年来在城市研究领域被重新发掘和引起热议的概念——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sation)[7]。
在这一系列讨论的结尾,列斐伏尔回到了更加抽象的维度,尝试对urban做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他宣称,城市是一个纯形式(a pure form),它是相遇之地、组合之所和共时性之处。这样的一个“纯形式”并不内蕴任何特定的内容,但是它又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和吸引力的中心环节。作为纯形式的城市(urban)是一个抽象物,但这个抽象物不是形而上的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抽象——它是始终由实践塑造着、并且不断反作用于实践的抽象产物。
四、空间与地方
与城市相关的第二个概念是空间。在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中,大卫·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空间分析框架[8]。具体来说,他认为我们对空间的讨论需要同时关注三个不同的类型或维度。
第一种类型的空间是绝对空间,也就是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牛顿和笛卡尔的空间。在这样的视野里,空间是固定的、静止的、可以切割的、可以测量的,是承载现实的容器,但它本身并不内蕴任何东西。比如,地址在英国这样的社会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固定的地址,在那个社会将没有立锥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在绝对空间的谱系里,对社会的规训和排序(social ordering)必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包括地籍测量和殖民制图术在内的空间治理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逐渐演化和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图景里,空间是固定和有边界的,所以可以用来承载土地所有权、承载一个人社会身份、或者承载一个殖民地的领土构建,这是绝对视角下的空间。
第二个类型是相对空间。近代物理学最大的进展是相对论的提出,在相对论的语境里边,焦点逐渐转向过程的和流动的空间。哈维在他的讨论里化用了物理学的分析视角,用来理解我们的社会变迁。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本地与远方的辩证法深刻地改变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它之所以能够如远弗届,首先借助的就是相对空间的建构——在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时代,当全球化的关联让地球变成“地球村”,跨越大陆和大洋的旅程从数月压缩到数小时,我们也同时能看到资本和信息的加速流通,最终走向哈维所界定的“时空压缩”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相对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哈维的框架里,第三个维度的空间是关系性的空间。在这个关系性的维度里边,我们要调转一下思维方式,不再把物质和过程视作存在于时空之中的某个东西;反过来,我们要把时空看作一种内在于物质和过程之中的事物,这个观点的哲学来源是莱布尼茨和怀特海。
举个例子,疫情时期在家上网课的时候,也许会有同学非常怀念校园景色和生活。当你怀念校园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开始回想春天里那棵热烈的玉兰——其实这个场景勾起的正是你对校园的某些特定的时空的记忆,而这样的特定的时空内在于那棵盛开的玉兰里。在你的记忆、你的思想、你的梦里边,那朵开了的花关联着并包含着一整个时空,而非相反。
我们也可以借用五条人在《世界的理想》里的一段歌词来做进一步说明:
请你不要再唱那些无聊的歌谣
理想的世界就躲在你的梦里面
那里的人们就像艺术家说的那样
人们自由自在地歌唱
牛羊自由自在地跳舞
在这个三维度的空间分析框架里,哈维最核心的论断是三个维度的空间缺一不可。当我们讨论任何一个空间议题时,都需要把这三个维度空间之间的张力及其辩证关系给放到中心环节。在哈维看来,空间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空间的特定概念化方式也会在同时构成我们定位自己的一个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与哈维一样,列斐伏尔也认为空间不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产物和社会构建,而且它自身也具有能动性,会制约着我们的社会关系与实践。在发展“空间的生产”理论时,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我们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切入他的三元论,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是从下面三个关键词入手: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
感知的空间关注我们的切身所感,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种空间触觉。云销雨霁,冷暖阴晴,玉兰花开,这些都是我们对空间的感知,也反过来形塑着我们的心情与生活状态。而构想的空间常常来自“遥远的目光”,投来目光的人往往并不触知特定的空间,但却意图按照自己的思路对描绘乃至改造这个空间。
典型的例子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的规划图纸。当市长和规划师们大刀阔斧地搞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新区和新城开发,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画一张“又新又美的蓝图”。绘制这张蓝图的人既不理解也不关心图纸所表征和想代替的空间实践是什么,人们对空间的触觉、期待和欲望又是什么,他们只关心所构想的那个空间的理念要如何在纸上再现出来,并且指导接下来的改造实践。
列斐伏尔最为激进的理念,植根在他对空间的第三个维度的阐释——生活的空间。这一维度不单纯是对感知的空间的复述,而是内蕴着创造性的政治势能。在他看来,我们需要集合起来,一起从构想空间的那些主体手里夺回我们对空间的自主感知。这个斗争的过程既是空间实践的过程,也是打破和重塑抽象空间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才能够摆脱资本和权力对空间的“生产”,重新让我们的生活得到立足之地。
多琳·马西延续了这样的讨论脉络,但又有自己的发展和创造。她在1990年代有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叫做“地方的全局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收录在1994年出版的《空间、地方与性别》[9]一书里。这篇文章的语境是当时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时空压缩”,就是我们把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压缩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相互之间距离更近的实体,从而加速资本和商品的流动,这是全球范围内资本循环得以加速的一个时空基础。
面对这样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在包括欧美在内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非常猛烈的反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的参与者常常援引海德格尔和他的“黑森林里的小木屋”隐喻。之所以要把目光转向这样的遥远僻静之所,是因为这些人相信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侵犯了他们对“地方”的占有,侵犯了他们所栖身的地方的“本真性”。
他们想把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加上高墙,阻止外在的全球性的力量的涌入,从而来保护自己内心的“平静”,而这正是马西写作“地方的全局感”时的靶子。她要批判和反思的就是对地方的保守解读,并力图进一步追问:我们是否可能构建一种外向型的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和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换句话说,我们的地方感是否可能不局限于特定地方本身,乃至跃出地方的边界?
马西在文章里的论述从她生前居住的地方展开——位于伦敦北部的基尔伯恩大街(Kilburn High Road)一带。在这条街上,你可以看到印度纱丽店、土耳其烤肉店、巴基斯坦餐厅,也能遇见拉美的各种小店铺、亚洲的中餐馆、韩餐馆、日料店。如果我们把这些店铺与他们的来源相结合的话,会发现在这样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上面,我们有机会看到几乎整个世界。
在这样的伦敦空间现实中,我们当然需要捕捉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殖民遗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投影,但同时也应当关注到那些缩微了的、全球化的本地现象。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超越这条大街本身的地理边界来重新概念化“地方”一词?
在马西看来,地方不应当是一个被高墙封闭的所在,而是一个相遇的地方(a meeting place),它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中相互连接的那些瞬间和时刻在当下的凝结。给予地方以其独特性的,并不是某些长时段、被内化了的历史,它事实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方式相遇并构建出来的。
基尔伯恩大街的确是伦敦的街道,也确实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领土,但它也是地球村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投影,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阶级的移民落脚之后相遇并且共同构建的地方。这些来自英国本土之外的移民正是构建街道本身地方感的关键主体。如果印度纱丽店、土耳其烤肉店和中餐馆都消失了,那么这条街道也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
五、空间与政治
在厘清了空间和地方的多重内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关键词:政治。空间与政治的关系是马西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里的核心关切。[10] 她与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保持一致,也同意空间是社会互动的途径和产物,同时又具有自己的能动性。而且,作为关系的产物,空间一直处于一种生成的过程之中(a process of becoming),所以它同时也凝聚了历史的动态和政治的可能性。鉴于此,马西提醒我们,对空间与政治之关系的解读,最终目标应当是构想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的空间观念。
面对写作时身处的1990年代,马西所做的时代诊断可以总结为三个原则:尊重差异、保持开放性和强调偶然性。她借助“权力几何”(power geometry)分析视角,尝试着用关系性的方式重新图绘特定的权力动态,继而从中引申出未来的政治的可能性。她的论述尤其关注不同的空间和权力关系如何差异化地塑造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和社会动态,并聚焦“空间化的社会权力”(spatialised social power)——也就是在特定的空间性被构建的过程中,内在于这个过程之中的权力关系,而非仅仅关注这个空间性本身。
马西的分析路径也呼应了福柯对权力的讨论。在后者看来,“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去检验和分析权力本身,诸如其起源、原则或合法的界限等细枝末节,而是去思考在不同的制度语境里施加在个体行为上的特定的权力方法与技术。这些方法与技术会形塑、导向、改变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最终指向的要么是这些人的沉默,要么被融入到更为宏观和总体性的权力策略(overall strategy)之中”(Foucault 1998: 463)[11]。
如果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三位思想家与福柯的建议结合在一起,那么“空间化的社会权力”就是一个合适的城市政治讨论的切入口,因为权力的空间方法和技术正是目前形塑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不得不戮力剖析的关键政治动态。我在《后厂村路上的北京折叠》一文中曾经对这一脉络的分析开展过初步的尝试:
我们能通过后厂村路识别出来北京甚至更宽广的时空中正在发生的几乎所有城市动态。它们在这里交汇,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分层和折叠的格局。而在这些城市动态彼此互动的所有环节,我们始终能发现同一个行动者的形象:它迁徙了 “蚁族”,改造了村民,鼓励了新秀,规训了码农,培育了新业态,生成了后厂村路上意料之外的密度,并采取措施整治这个 “意料之外”。在各式各样密度被不断取消和生成的拓扑格局之中,始终不变的是这位行动者的直观功能——一种空间化了的权力。正是在其主导的多重密度化和去密度化过程相互交错之时,我们的城市境况被不断改写。也许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直至郝景芳预言的那个被折叠的未来最终到来……
这样的分析思路属于城市政治学吗?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本《城市政治学理论》并无法帮助我们去把握这种空间化的社会权力。我们的城市境况要求在智识层面继续质询politics of the urban——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列斐伏尔、哈维和玛西关于城市、空间与政治的讨论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对话,而且还需要做进一步拓展。
对中国城市动态所做的分析一定有潜力帮助其他语境下的读者理解他们各自的切身处境,并推动城市问题的进一步概念化和理论化。当我们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南方”经验并置在一起,一种更加全球的城市研究(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也才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而这也正是“以世界为目的”的题中之义。
换言之,我们需要“城市政治学”,但必须是更新和改造了之后的“城市政治学”,是一种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城市政治学。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开设的《城市政治学》课程第一讲录音,有删改,感谢魏航、朱戈协助整理课程录音】
[1] “增长机器”的主要内涵是,为了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的增长目标,一个城市的若干精英可能会结盟,会去共同利用各自的资源捆绑在一起,实现他们共同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增长机器。参见Logan, J. R., & Molotch, H. (200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城市政体理论在增长机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关切城市决策背后更为宏大、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存在,认为是这些网络的互动才最终决定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效果。对比来看,增长机器框架里面的权力,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power over something),而城市政体理论里面的权力被重新概念化了,不再是控制的手段,而更强调其“能力”(power to do something).
[3] 沟口雄三. (2011). 作为方法的中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参见「城识」推送:《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
[5] Harvey, D. (1996). Cities or urbanization? City, 1(1–2), 38–61.
[6] Lefebvre, H. (2003). The urb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直接阅读英文版。
[7] 参见「城识」推送:《“星球城市化”:城市理论的边缘与前沿》
[8]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9]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0] Massey, D. (1999). Spaces of politics. In D. Massey, J. Allen, & P. Sarre (Eds.), Human geography today (pp. 279–294). Polity Press.
[11] Foucault, M. (1998). “Foucault.” In James Faubion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pp. 459–464). Penguin Books.